Many happy returns homestay
1 noche
Habitaciones y huéspedes
1 habitación, 2 adultos, 0 niños
Todos los alojamientos en Shangri-La
Many happy returns homestay
No.43 Shenying Road, Shangri-La, Yunnan, China
Ver mapa
Igualamos los precios

Última reserva en Trip.com hace 30 min






 Información destacada
Información destacada Servicio de enlace con el aeropuerto gratis
Servicio de enlace con el aeropuerto gratis Desayuno variado
Desayuno variado Muy limpio
Muy limpio Ubicación excelente
Ubicación excelente Aparcamiento gratuito
Aparcamiento gratuitoMostrar más
Instalaciones y servicios
Aparcamiento públicoGratis
Consigna de equipaje
Servicio de despertador
Servicio prioritario de recogida en el aeropuertoGratis
Wifi en zonas públicas
Servicio prioritario de traslado al aeropuertoGratis
Restaurante
Servicio de recogida en la estaciónGratis
Todos los servicios
Descripción del alojamiento
Find some B&Bs on your way and stay to feel the original sponsorship life. Experience proves enthusiasm. Welcome friends from afar to find the teacher and the distance.
Mostrar más
9.9/10
PerfectoLimpieza9.9
Instalaciones9.9
Ubicación9.9
Servicio9.9
Todas las valoraciones (278)
Alrededores
Aeropuerto: Aeropuerto Dêqên
(1.5 km)
Tren: Shangri-la Railway Station
(4.1 km)
Tren: XiaozhongdianRailway Station
(34.5 km)
Lugares de interés: Large Prayer Flags
(1.0 km)
Lugares de interés: Colorful Hada Tibetan Di Performance Park
(1.2 km)
Lugares de interés: Dukezong Ancient Town Gate
(1.8 km)
Ver en el mapa
Información general
Habitaciones
Valoraciones de usuarios
Instalaciones y servicios
Políticas

7
Habitación con cama grande y vista
1 cama doble grande
20-25 m² | Planta: 1-2
Con ventana
Internet por cable gratuito
Se permite fumar
Aire acondicionado
Baño privado
Vistas a la montaña
Toallas
Comprobar disponibilidad

6
Habitación con 2 camas y vista
2 camas individuales
25-30 m² | Planta: 1-2
Con ventana
Internet por cable gratuito
Se permite fumar
Aire acondicionado
Baño privado
Vistas a la montaña
Toallas
Comprobar disponibilidad
Valoraciones de usuarios
9.9/10
Perfecto
278 valoracion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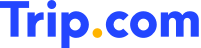 Valoraciones reales
Valoraciones reales- Limpieza9.9
- Instalaciones9.9
- Ubicación9.9
- Servicio9.9
Calificación media de alojamientos similares en Shangri-La

Usuario invitado
26 de julio de 2025
推開那扇繪着彩色祥雲的木門時,青稞酒的醇厚香氣先一步漫了出來。藏族老闆扎西正舉着銅壺往火塘邊的陶碗裏添酥油茶,見我們進來,立刻放下壺迎上來,黝黑的臉上堆着笑,藏袍袖口隨動作掃過門楣上掛着的經幡,簌簌落了些陽光的碎屑。
“呀,你們可算到了!”他的普通話帶着點藏語的尾調,像加了蜜的酥油茶,“路上累壞了吧?快坐快坐,我讓卓瑪把烤好的氂牛肉端來。”火塘裏的牛糞火噼啪響着,把整個堂屋烘得暖融融的,牆上掛着的唐卡在火光裏浮動,觀音的衣袂彷彿都在輕輕飄。
進房放下行李才發現,鋪着藏毯的床尾疊着兩床厚棉被,卓瑪——扎西的妻子,正踮着腳往窗台上擺一小盆格桑花,見我們進來,紅着臉遞過兩個牛皮紙包:“剛烤的糌粑,路上餓了能墊墊。”紙包裏混着酥油的香氣,讓旅途的疲憊都淡了大半。
傍晚去轉經回來,遠遠就看見屋頂的煙囱冒着白煙。扎西正蹲在院角幫我們擦沾滿泥的登山靴,見我們回來,直起身拍着手笑:“卓瑪燉了松茸雞湯,你們轉經辛苦,得多喝兩碗補補!”飯桌上,他給我們講納木錯的傳説,講藏曆新年時的鍋莊舞,講到興起處,還從櫃子裏翻出青稞酒,非要和我們碰杯,酒液滑過喉嚨,帶着陽光和高原的清冽。
夜裡起風,正擔心會冷,就聽見門外有輕響。披衣出去看,扎西正往門框上掛厚氈簾,見我出來,指了指天上的星星:“今晚風大,但星星亮,你們要是想看星空,我給你們找手電筒。”他的身影在月光裏被拉得很長,藏袍的邊緣沾着草屑,像剛從草原上回來。
離開那天早上,卓瑪天沒亮就起來烙餅,扎西幫我們把行李捆在車頂,還往背包裏塞了一小袋風乾氂牛肉:“路上吃,比餅乾頂餓。”車開出很遠,回頭還能看見他們站在門口揮手,經幡在風裡獵獵作響,像無數雙捨不得的眼睛。那間藏式民居里的暖意,混着酥油茶、青稞酒和松茸的香氣,成了高原之行裏最温軟的記憶。
Traducir

Shupangxiedezhangxiaoliang
25 de julio de 2025
民宿位置鬧中取靜,是熱情好客的本地人自己的家,裝修豪華氣派,一定要參觀一下他家二樓的客廳,我家小朋友進去直呼“太漂亮啦,不想走啦”。
房間很大,打掃得很乾凈,整個家都很乾凈,洗衣機也很乾凈,兄妹倆勤快得很。早上主人家準備了豐富的藏餐,吃得很飽。建議大家試一下鹹茶,淡淡的鹽味,感覺比甜茶好喝。吃完飯小哥哥送我們到動車站,非常感謝。
Traducir

Usuario invitado
24 de julio de 2025
從環境到服務完全都是超預期的存在!民宿環境很好,房間很大,從窗户能看到非常美的景色,是整個雲南之行中最滿意的一次住宿。最最重要的是,老闆人非常nice,知道我們趕早班高鐵,提前準備好了熱乎乎的早餐,讓我們打包到車站。我們當時想要去無底湖,老闆主動幫忙聯繫靠譜包車司機,還送我們去了古城乘車,人情味滿滿❤️❤️ 第一次上高海拔地區,在香格里拉能遇到這樣的神仙民宿,絕對是旅行加分項~強烈安利給所有想來玩的小夥伴,閉眼沖就對了!
🏡老闆一家都是藏族,尤其年輕的老闆,有一種獨特的藏地帥氣,頗有香格里拉彭于晏的味道🥳🥳
Traducir

Usuario invitado
22 de julio de 2025
先説結論:個人認為應該是這個價位最好的一批民宿之一
設施:房間寬敞美觀,有大電視機、加濕器、熱水壺、空調和電熱毯,無論冬夏都能有比較舒適的入住體驗。還有一個小圓桌可以用來喝喝茶、欣賞欣賞風景或者玩玩電腦。
衞生:非常乾淨。床上用品也是嶄新的。
環境:有點偏,主要是不好找地方吃飯。但是離古城很近,打車也就十幾塊。也可以租車,附近就有,來香格里拉還是比較推薦租車的。環境特別清凈,適合想要好好休息或者比較i的人,有一種遺世獨立的感覺。而且周圍風景很不錯。
服務:服務特別好。小哥哥小姐姐都特別熱情,有接送服務,每天還有免費早餐。
Traducir

Usuario invitado
19 de julio de 2025
特別好的老闆,很熱情好客 我們上午剛剛到達 還沒辦理入住 老闆就幫我們準備了早餐,提供的礦泉水是農夫山泉的 沒有用雜牌子,房間很乾凈整潔 空間也很大 院子很漂亮 很有民族特色 老闆還主動把我們接送到高鐵站 還為我們推薦了景點 早飯做的很好吃 有當地的特色酥油茶 離獨克宗也挺近的 下次二刷還來! 很棒的民宿
Traducir

Usuario invitado
14 de julio de 2025
民宿非常不錯呀 環境非常好 房間設施也蠻不錯的住的很舒服 老闆非常熱情 一直都有接送的服務 我們第二天一大早的高鐵 老闆還給我們準備了早餐 而且這裏離古城納帕海這些景區也不遠 挺方便的 推薦推薦~~~
Traducir

Usuario invitado
21 de julio de 2025
來香格里拉被這家民宿吸引,有接送站的服務。
老闆非常熱情好客,還幫我們拿行李。每天早上還有當地特色的早餐,老闆自己做的油酥茶比店裡的好喝多了,有機會冬天再來一次,讓人捨不得離開的地方,超棒!
Traducir

Usuario invitado
13 de julio de 2025
老闆非常熱情,早餐非常好吃,還帶着我們去草原玩,環境也是我這次來雲南中特別好的,民宿裏還有藏式客廳可以參觀(非常的豪華呀)可惜這次時間比較趕,如果以後有機會還會再來!最後一天車比較早,帥哥老闆説自己五點多就起床了,太感動了!(店裡的貓咪也非常可愛,齊劉海非常萌😻,還愛吃玉米)
Traducir

Usuario invitado
24 de julio de 2025
藏式住宅,自己家的大院,停車非常方便,離古城並不遠,開車5-8分鐘左右就到了。民宿主人一家非常熱情好客,服務上可以説是有求必應,對了還有他家大貓瑤瑤,可愛的很,隨便擼的那種
Traducir
Instalaciones y servicios
Servicios y prestaciones más populares
Aparcamiento público
Gratis
Consigna de equipaje
Servicio de despertador
Servicio prioritario de recogida en el aeropuerto
Gratis
Wifi en zonas públicas
Servicio prioritario de traslado al aeropuerto
Gratis
Restaurante
Servicio de recogida en la estación
Gratis
Zona para fumadores
Lavandería

Restaurante
Restaurante
Restaurante
Restaurantes: Solo para los huéspedes del alojamiento
Más servicios
Internet
Wifi en zonas públicas
Aparcamiento
Hay A disposición del público disponible En el alojamiento. No es necesario reservar.
Aparcamiento público
Gratis
Servicio de aparcacoches
Gratis
Transporte
Servicio de recogida en la estación
Gratis
Servicio de traslado a la estación
Gratis
Servicio prioritario de recogida en el aeropuerto
Gratis
Servicio prioritario de traslado al aeropuerto
Gratis
Servicios de recepción
Recepción (horario limitado)
Registro de entrada y de salida exprés
Consigna de equipaje
Servicio de despertador
Comida y bebida
Bar en el vestíbulo
Servicio de habitaciones
Zonas comunes
Zona para fumadores
Sistema de sonido
Humidificador
Cocina compartida
Servicios de limpieza
Lavandería
Servicio de lavandería (en el alojamiento)
Gratis
Detergente para ropa
Accesibilidad
Pasamanos en las escaleras
Seguridad
Botiquín
Sistema de acceso con llave tarjeta
Circuito cerrado de televisión en las zonas comunes
Extintor
Políticas del alojamiento
Hora de entrada y de salida
Hora de entrada: a partir de las 14:00
Hora de salida: antes de las 12:00
Horario de recepción: [lun-dom]05:00-23:59
Admisión de huéspedes
Este alojamiento solo admite huéspedes que sean titulares de un permiso de viaje, un permiso de residencia o un documento de identidad expedido en China continental.
Políticas sobre admisión de niños
Este alojamiento admite niños de todas las edades.
Los niños de entre 0 y 17 años pueden alojarse gratis si no necesitan cama extra.
Cunas y camas extra
No es posible añadir cunas ni camas extra en ningún tipo de habitación.
Desayuno
Tipochino
TipoMenú fijo
Horario de apertura[lun - dom] 08:30-10:00 Abierto
| Edad | Cargo |
|---|---|
Adulto | Contactar con el hotel |
El precio de los desayunos adicionales no se incluye en el importe total de la reserva, y debe abonarse en el alojamiento.
Política de depósitos
DepósitosEl alojamiento no requiere depósito
Mascotas
No se admiten mascotas
Requisitos de edad
El huésped principal que haga el registro de entrada debe tener al menos 18 años.
Pago en el hotel



- Efectivo
Descripción del alojamiento
- Inaugurado: 2022
- N.º de habitaciones: 8
Find some B&Bs on your way and stay to feel the original sponsorship life. Experience proves enthusiasm. Welcome friends from afar to find the teacher and the distance.